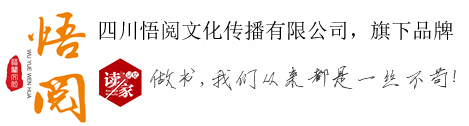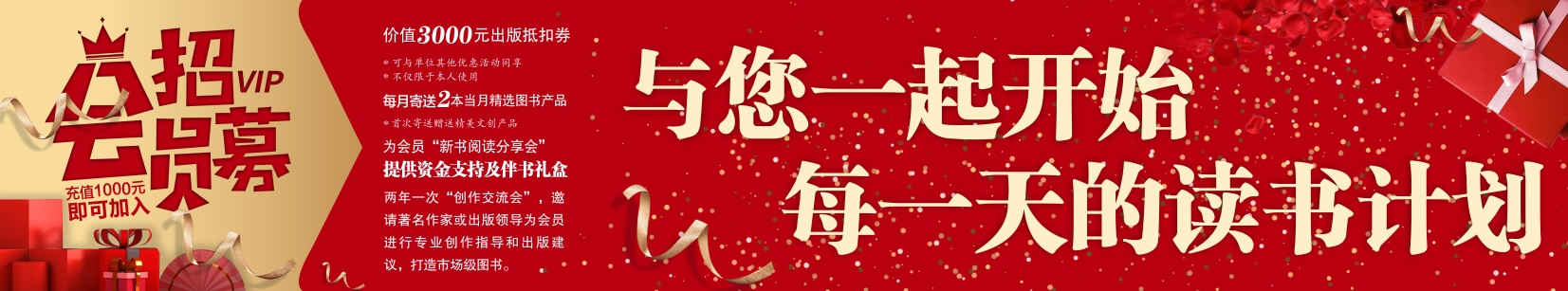028-86613050
18581836866
精彩书评
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 精彩书评
情满山川意盈灵(序)
孟德明
关于游记,我曾为武汉作家何蔚的文章写过一篇评论《游记该往何处写》,实在是流露着我对于游记写作的一份困惑,也试图通过何蔚的“新感觉游记”寻得一些当下读者较为认可的方法。
中国幅员广阔,山川奇景众多,总在引领人们向往外面的世界,即使古代交通不便,依然激发着他们的踏勘欲望,长途跋涉、不辞艰辛,就为留下些足迹。更受到文人的青睐,激发出他们的诗情笔意,纷纷付诸文字,或摹景色之美,或抒胸中情怀,或感喟人生启悟。由此,就出现了谢灵运、郦道元、李白、徐霞客等旅行家兼诗文大家,成为一世高标,也以此标识着我国游记文学的根深文脉。
文脉可续不可断,可新不可守。这里,我们不得不发出感叹,当人类的开掘技术足以先进时,许多的奇峰在我们这一代被开发未必是件好事。我们应该给后代预留些山水空间,因为现代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给人文传承造成强烈的冲撞。不能否认,从前游记的盛行,除了这种文体的文学意义,也有旅游的功能在的。现在,还有几个人会通过一篇游记去了解一处景物呢?只要网上一搜索,大量的图片就让人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即使那些偏僻的景区到旅游旺季都是人头攒动,什么火焰山、珠穆朗玛、喀纳斯湖,都没有了神秘感。而以前人们靠脚力行走得到的风景毕竟有限,对于他乡景致的了解就要靠阅读得到。当然,游记不是景点的说明书,它更侧重文学意义。风景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更是一笔宝贵财富,那庄子想象中的昆仑、李白笔下的瀛洲、卢仝向往的蓬莱,抒发的是一种由已知大胆探索未知的情怀。
其实,古代那些游记中的泛泛之作早已被淹没,我们今天读到的佳作都是沙里澄金的遗存,也被称为了名篇,各有所长。若说以景言志,当属王安石和范仲淹。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表达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感慨;范仲淹《岳阳楼记》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志向。以山川言志,是一着险棋,除了名家高手,不是谁都可以落子的,闹不好就流于空泛。平心而论,这些年的阅读,我对于游记写作产生了些许“抗体”,我看到那些时间地点、加上一堆形容词的套路式写作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我断定这是平庸的写者。
可喜的是,在今天游记写作空间不大的前提下,依然涌现出一些有志者,秉持着久远的传承,常常以新的姿态,营造出让我们眼睛一亮的艺术境界。作家何蔚的“新感觉”靠着那股通透的诗性取胜,气韵十足,所以我为他点赞。在读了作家邹安超的游记后,她文字中流露的执着的古典情怀,又能让我眼睛一亮,我的警觉的阅读还是被她的笔墨打动了。这也是在她的新书《用花开的心情去远方》出版之际,我愿意写些感想的缘由。
我们的内心都有两个家园:一个是生活家园,是一个人生长生活的地方,那是根基,是寄托,长大后会有种“乡愁”的滋味;一个是向往家园,即他乡风景,总是引领我们的好奇心,愿意作短暂的客居,每每试图走近,让单一的生活得以滋补。
读邹安超的游记,我很留意每篇文章的开头,聪颖的她没有按照传统的“移步换形”的手法交代她游走的时间与景色,她似乎是有意回避,她深知,这些仅仅是她自己关心的,往往对于读者的阅读启悟不大。她一般不会告诉你,是遇上了雨还是赶上了风这些偶然的天气因素;是没赶上车还是刚吃了早饭这些游玩琐事。在她看来,不能代表一个地方的风度与气质的材料一定要舍弃。她善于在开头就给全文定下基调,展示我们所说的“文眼”。要知道,这样的行文体式说来容易,实施起来却不易。我以为她也是在有意为自己的写作设置“障碍”,增加作品陌生感,因为它会限制素材的运用,意味着必须重新梳理素材,很多好玩却“无意义”的要被去掉。而这也正是她文章的成功之处。试举几例:“水蹴就了周庄。否则,就遗失水乡的称谓了”(《水韵周庄》);“静。很静。这样的感觉从感官传达到神经”(《盛夏,木格措的静》);“夜的西湖,让人迷离”(《西湖的魅》);“最先抵达是水声。寻着声音,几步就靠近水边,才发现面前是一挂水瀑”(《双龙桥的水》)。寥寥数笔,就为全文确定了基调与走向。读她的散文,首先感受到的是美质,如一件瓷器那样的美质,它玲珑、温润而又浑然一体。全文便在一种基调下平稳运行,不用担心她会出现行文结构或者语言上的闪失,她会沿着自己独有的感悟前行,架构一篇文章。
说到散文,就必须说说语言。我读一些人的文章,就常会读出那种语言的漂浮感,热闹在外,内里却很空乏。试想,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够走远?汪曾祺对于语言有很好的见识,他说:“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那么,邹安超又有着怎样的语言运行模式呢?纵观她的文章,她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以情融景,以言化境,深得古代诗文的熏染。透过一篇篇作品,我们能看到一个身着锦绣、轻摇罗扇、小家碧玉的女子在沉醉于山水景色,而此时她又恰好也走进了这幅画卷。所以说,邹安超的散文极具画面感,她喜欢使用浓墨描画,把江南的湖光山色尽情地收进画稿。她的词语既是古诗词的化用,又融入了当下生活化的语言,我们能读到她运用长短句的节奏感。通篇来看,她所运用的手法并不是急于跟风,也不使用外来的那些变形夸张之类的技巧。她始终沉着地表现着她眼里的景物世界。我们看:“这幅丹青,不用浓墨重彩,只须轻轻地点几笔,用工笔画的架构,把远处的农舍,近处的田埂,一弯正在绽放的油菜花和几簇胡豆花,再摆上那一横一竖的桥面,一方一圆的桥洞,寥寥几笔,取个与陈逸飞《故乡的回忆》同名同姓的画名”(《南充:青山湖之上》);“春天,生机之时,也是自然界中经受过寒冬摧残的生命原色萌动之时,然后才有小草泛着铮亮颜色的绿,也才有嫩绿青翠吐露着清新气息的滋养和新陈代谢的更迭”(《绿色恩典》)。她的笔端有一种韵律,我以为更像是宋词的化用,让人阅读时很快就会在长长短短的句子里找到共鸣。
游记是座富矿,却是在当今条件下难以开采的富矿。邹安超以典雅之美、曼妙之笔,执着于她的山水行走中。相信她瞄准自己的书写风格,在凝练与张力上做足文章,一定还会有更好的美学展现。
(孟德明:“新荷花淀写作”领军人,河北省廊坊散文学会会长,冰心散文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