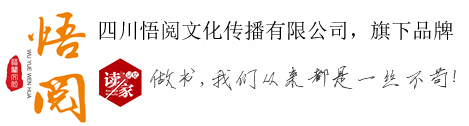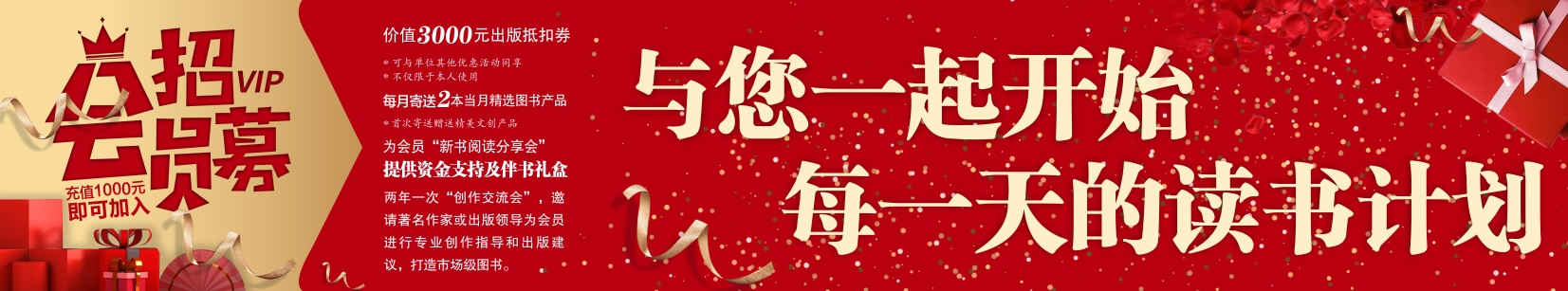028-86613050
18581836866
精彩书评
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 精彩书评
山水宜宾(代序)
宜宾的江浩浩乎!宜宾的山巍巍乎!
从格拉丹冬雪域流来的金沙江,从“更喜千里雪”的岷山流来的岷江,在宜宾城区中心的合江门处合二为一成为长江。不仅如此,宜宾的河有九河,南广河、关河(即横江)、越溪河、长宁河、西宁河、黄沙河、古宋河、箭板河、宋江河,以及注入三江九河的那些数都数不过来的小河小溪。岂不说北方,这想都不要想。即使是在南方水网密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一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拥有如此众多的江和河,可以肯定地说是罕见的。这是天赋宜宾,也是宜宾人的福分。
逐水而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类智慧的重要表征。《周易·大传》里即有“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的高度概括。宜宾城是一座典型的因水而生、因水而在、因水而长的城市。宜宾人得益于三江九河在这块土地上建造着自己的家园,创造着自己的财富,丰富着独具魅力的文化。岷江,由北向南,顺流而下,滋养川西平原,滋养嘉州,然后平平缓缓流进到叙州。岷江对于宜宾来说,从物理角度来看,它源源不断的水滋养着宜宾县沿江两岸的庄稼,特别是它作为宜宾与成都与岷江沿岸城镇村庄的商业贸易重镇,是宜宾最早和最重要的贸易孔道。但仅这样认识岷江的作用,显然是太对不起这条在清代之前还被认为是长江干流的岷江了。从宜宾的文明进程和文化传承来讲,岷江是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在宜宾的连结。至少从唐就开始的岷江河运,让大唐的文化顺流而下,感化着当时还稍落后的戎州文化。一代诗圣杜甫在锦城浣花溪畔吟诵的“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船,从浣花溪出发,经九眼桥、黄龙溪,过乐山,然后从宜宾发往东吴。史载及杜诗中,就有过地方绅士专门于江边东楼宴请杜甫而杜甫赋诗的风流!到北宋黄庭坚谪居戎州,由于宋文化政策的宽松,特别是由于一代文豪黄庭坚于宜宾三年的“教化”,宜宾的文化突飞猛进。在黄庭坚离戎(1100年)后不久(1114年),大宋中央王朝便改县名僰道为宜宾,改州名戎州为叙州。这两次改名,是宜宾文明史的大事件和转折。得益于岷江——它给宜宾的文化注入了新机,促进了繁荣。
再说金沙江。如果说宜宾的文化是由成都传入,宜宾作为接受地,那么宜宾以南的文化则是由宜宾向外传播所形成的。新近中央博物院、四川博物院、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和宜宾市委宣传部联合对秦汉“五尺道”的考古则表明,自秦朝开始,中央政府从政治上加强了对边地的管制,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加强了交流。在经济方面,到清末民初,一句“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便是最好的注脚。文化方面,仅从酒史来说便可见一斑:两千多年前的“枸酱”发端而开始的宜宾酒业和酒文化,两千多年以来延绵不绝、时酿时新,照亮着中国酒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屏山为中心的金沙江下游的文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记载。特别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中原文化全面接管了原来还属边地的文化。随着向家坝大坝的建设深入,以屏山为中心的金沙江下游的地上地下文化遗迹遗存,越来越引起关注。新近在屏山的叫花岩的考古中发掘到4000多年前的一具陶质酒具,更把宜宾的酿酒业和酒文化推前了一千多年。像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的“金江号子”则唱出了金沙江下游船夫们的艰辛与欢乐。
得益于岷江与金沙江在三江口的合流,宜宾的独特的多元文化成为“西南半壁”文化融化的象征。
宜宾九河中的四条河不得不提。——越溪河、关河、长宁河、南广河。越溪河流经川南农耕发达的荣县、宜宾县。这条河不仅自古就是荣县川盐出川的重要通道,而且是两宋时期宜宾的文化高地。由宋真宗亲赐匾额的“蟠龙书院”,始建于998年。此后历代相续相继,书声不断,人才精进。有一门三进士的程氏兄弟出现,此虽不及眉山一门三学士那样名留千古,但当时亦有诗称颂为“三川震动”。当下临河的隆兴一带的无数古迹,隐隐约约显示着昔日的荣耀;关河,虽不像越溪河那样有文化,但是作为自宜宾到云南的主通道,经济贸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关河边的重镇横江古镇的气派、石城山的崖刻,风韵依然。“五尺道”考古的专家们于此流连忘返;长宁河在宜宾境内流经三个县,即珙县、长宁县、江安县,在明一代,长宁的两位进士,高居榜眼,其中周洪谟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南广河,作为宜宾的“母亲河”则显现出它从古而今的作用。在秦汉的“五尺道”“南夷道”是水陆的重要连结线,在宋明的“茶马古道”是水陆连结线,在清民的“叙滇官道”“叙昆大道”是水陆连结线。这条纵贯宜宾南六县的南广河,两岸的村落集镇、渡口码头,记录着明万历初年运官兵征剿都掌蛮的历史,记录着清代运输滇铜、川盐的历史,记录着民国交易山货洋货的历史,记录着两岸人民辛勤劳作的历史……记得在第一部由中日合拍的《话说长江》(1983年)的光影记录里,宜宾一段,最多的记录和最长的记录就是南广河的风景。那清越的水声和那浑厚的解说词直到今天,依然是那样的悦耳、那样的生动和那样的充满活力。
当然,宜宾的山也不逊色于宜宾的水。
从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宜宾的山不仅拱卫着宜宾,其实也拱卫着四川的南大门(准确地讲是东南大门)。也就是说,宜宾的山就是四川盆地的东南边沿,越过这些山,或爬上这些山,就是云贵高原了。屏山县的老君山2008米,是川南的最高山峰。在宜宾境内1500以上的山峰有近10座。现在就来说说老君山。“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老君山的:“老君山为川南第一峰,海拔2008.7米,环绕老君山分布的原始森林约1万公顷,是四川保持最好的、川南唯一的亚热带原始林区。林区内树种在3500种以上,超过了峨眉山。林区内飞禽走兽1000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有300多种,如飞貂、金钱豹、黑熊、小熊、红腹锦鸡等。”而“屏山鹧鸪”(学名“山鹧鸪”)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鹧鸪品种。与老君山同一纬度和海拔相差无几的,在宜宾还有筠连的大雪山(1777米)、珙县的四里坡(1642米)和兴文的先峰山(1795米)。这些都在北纬28度。众所周知,北纬28度地区的原始森林,在世界范围早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在宜宾就有成片的两片!像濒临绝种的珍稀树木珙桐,在老君山、大雪山和四里坡都是常见之物。与恐龙同时代的桫椤树,在宜宾的北纬28度的丹霞地貌上到处都是,集群上万株就有几片!
这还只是宜宾群山植被的大概描述。这些山的下面则是宜宾富藏的矿产资源。其他的不多说,就说煤和盐。宜宾煤的储量占四川的前两位。筠连与邻县叙永(泸州市叙永县)的煤田是四川现在最大的媒田。仅筠连的优质无烟煤可采储量就高达28.12亿吨。除了电煤外调,宜宾在2010年年底和2011年年初的两座装机分别为120万千瓦的火电厂的电煤,全部都来自宜宾本土生产的煤!宜宾盐的储量更是高达100亿吨以上。差不多就是第二个“盐都”了。
当然,宜宾的山不仅是绿色自然的山,也是文化悠久的山。
老君山是一片原始森林,它的脚边建于后蜀(934—965年)的古镇龙华,迄今已有一千余年历史。古镇虽经风雨,但明清时的街道格局依然清晰、明清典雅古朴的串架木房依然矗立山脊。绕镇而流的大小龙溪,硕大无朋的黄桷树、斑驳的风雨桥,无处不显现出古镇的风流。而风雨桥上的历代匾额,彰显出龙华古镇的悠久文化传承。有意思的是,不仅在老君山的顶峰,游人可以看见不知何年修筑的老君庙,而且在八仙山,我们可以一睹华夏大地仅次于乐山大佛的弥勒佛的伟岸与雄姿。其实在宜宾的大山中,更值得宜宾人骄傲的是隐藏着或完整或残缺的“五尺道”遗址遗存。筠连的大山里,雄立于险隘高垭上的明代凌云关、隐豹关,以及关上的模糊的题刻,表明了大山里的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古道,至今还为当地进山出山的百姓承担着古道的责任。这是了不起的事件,这是了不起的历史!
在宜宾城区的翠屏山真武山(事实上这是一座山,临金沙江一边叫翠屏山,临岷江一边叫真武山)。有人说宜宾城区的翠屏山真武山是仅次于南京钟山的第二大城市森林公园。我不知道钟山的面积,但我知道翠屏山真武山的面积近5000亩。除了古树参天、林荫匝地之外。翠屏山的千佛崖是唐人的遗韵,翠屏书院则是明人的作品。而真武山却是宜宾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见证。真武山自东汉始因张道陵传道就注入了文化的因子,宋称仙侣山,后称师来山。明万历元年(1573),明皇室做出了对宜宾以南的“都掌蛮”弃“抚”进“剿”的重大决策,一改明两百年来对“都掌蛮”“抚剿并举”但以“抚”为主的国策。终于,在万历元年进“剿”取得重大突破。至此,从秦汉世代生活于川南与一带的“僰人”,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殆尽而成为至今未解之谜。翌年即明万历二年(1574),四川抚军曾省吾(即“剿总司令”)在师来山上大兴土木,以志天恩,以彰功勋。这就是著名的《修真武山祠记》。在这篇“记”里,曾抚军称,他在万历元年七月征战九丝城正酣时,病中有人托梦,说是有天上真武大神助力,大功告成,路经叙州返成都时,拜谒真武山,“追忆曩梦”,深感“天人之际”,于是修祠勒石作记。此后,修葺和扩张真武山的庙宇,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同事业。今天我们所见建筑式样和宏大规模,大都在清末建成。从明到清,历朝官员文人,留下了许多专为真武山而写的诗文。其中官至康熙翰林、山西布政使、宜宾土著胡瀛的一首七言古风《游师来山》就很有名。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洞亭敞敞七星朝,宫阙荧煌插汉霄。降魔作镇驱妖嗥,驾鹤真人俯江皋。”从诗中我们看到,真武山有关神仙的传说,不仅早已有之,而且在诗人眼里,还真有其事呢!我们还看到,真武山的庙宇,在清已蔚为大观了。另外,与真武山和真武山庙宇相关相连的其他景点和建筑相映成趣的如仙侣洞、郁姑台、遇仙楼等被发现、被建造了起来。号称“川南道教名山”,历来就有“北有青城南有真武”之说。由岷江江边一阶一步到达山顶,参天古树掩映,三座大石坊分别名为头天门、二天门、三天门。若干年以来,香火缭绕,道音清心。
得益于宜宾的水,得益于宜宾的山,宜宾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得益于宜宾的水,得益于宜宾的山,“山水宜宾”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