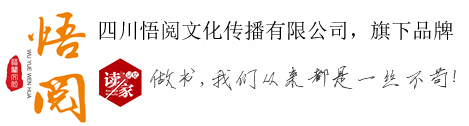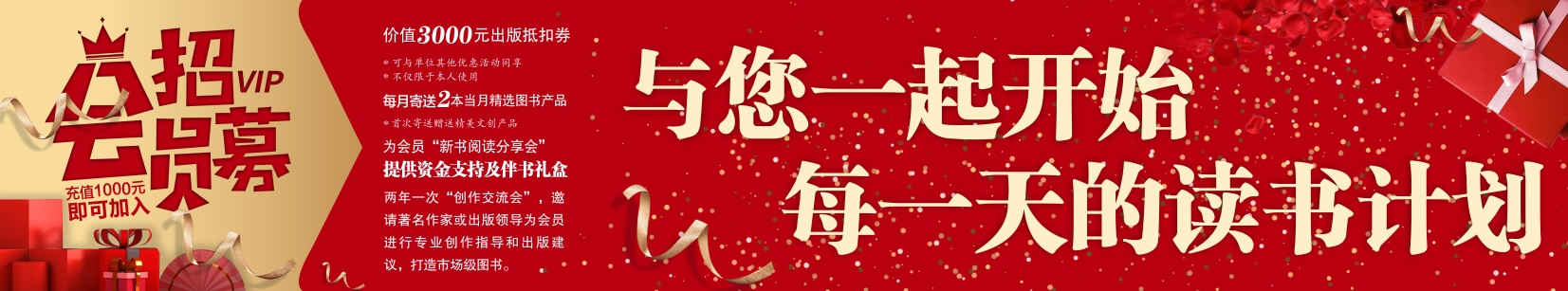028-86613050
18581836866
精彩书评
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 精彩书评
《人生的曼妙时光》序
在文学中传递温暖
◎ 赵克红
今年春天,洛阳石化的吴文奇先生,被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录取,喜讯不胫而走,在洛阳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喜爱文学的人大都知道,鲁迅文学院被誉为作家的“黄埔军校”、“文学的殿堂”。到鲁院学习,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梦想。由于条件苛刻,名额有限,能被鲁院高研班录取的学员,可谓凤毛麟角,这也印证了吴文奇先生的实力(据我所知,自2002年高研班建立至今,文奇是洛阳十五年来的第二人)。
尽管文奇先生是中国石化作家协会推荐的,但他出生和工作皆在洛阳市吉利区,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同时,他还是我们洛阳作家协会的理事、副秘书长,因此,这也是我们洛阳的一份荣耀和光荣。
对于文奇我是了解的。作为石化职工,他闲暇之余,笔耕不辍,围绕石化中心工作,紧扣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创作了大量讴歌石化工人以及洛阳的文学作品,连续获得中国石化文学大赛奖项,并出版有小说集《我的红灯记》,在中石化系统内外颇有影响。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曾经并依然对华夏民族有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影响。河洛地区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河洛文学是河洛文化中绚丽多彩的组成部分。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学的中心,自古人杰地灵,文人辈出。《尚书》开中国散文作品之先,《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中的不少篇目,《诗经》中的不少诗作,代表着河洛文学的最初成就。西汉时洛阳人虞初著《周说》被誉为小说的开山之作。汉代辞赋,建安文学,汉魏文章,唐诗宋词,成就了河洛文学的辉煌。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等无以计数的文人名流或诞生于此,或生活于此,或终老于此。历经千百年文气雅风的熏陶滋润和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以来,曹靖华、李准、葛洛、时乐蒙、吉学沛、陆柱国、扬子敏、阎连科、张宇等等更是从洛阳走向全国,享誉海内外。目前,尽管市场经济的潮声掩盖了少许文学的声音,但洛阳还是有一大批作家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梦想,坚持着文学创作。可以说,我们洛阳的才子佳人,历经风雨,笑对彩虹,胸中自有日月星辰,笔下更生花波蕾涛。
自然,文奇也是其中的一员。
今年5月8日,我从洛阳专程到鲁院看望了文奇。当时,他依然难掩激动之情,他对我讲,他正在整理撰写一本鲁院笔记,我听后表示赞同,但并没太在意。几天前,当他将这部书稿真正放到我案头之时,我颇为欣喜和惊讶。欣喜的是文奇学有所获,不负众望;惊讶的是,在鲁院文奇学习任务繁重,除了这本书,他还创作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他哪来的时间和精力?于是,我放下手头所有的活计,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渐渐地我被这本书牢牢吸引。这部散文随笔集写得有点另类、有些与众不同。这本书采取了日记体,以作者自身为主线,一天一记,全景影像般、立体式地介绍文奇在鲁院高研班的学习、生活状况。全书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写了作者自己在鲁院的经历、以及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二是学员的研讨发言和鲁院论坛等相关活动的情况摘要;三是授课老师的介绍以及讲课内容的要点。“观一斑略知全豹”,看了这本书,从中不仅了解到了鲁院“高研班”的学习情况,而且也得到了许多新颖的文学理论和观点的启迪。多年来,我身边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向往鲁院,但由于名额所限,无法前往培训学习。因此,大家渴望了解鲁院以及高研班的一些情况。文奇来自基层,清楚基层文学爱好者想知道什么、了解什么,因此,他这本书似乎就是专门为那些怀揣文学梦想、渴望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们精心打造的。
读了文奇的这部书,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奇的了解。
首先,文奇不仅爱他的企业,也深切炽热地眷恋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洛阳。在开学做自我介绍时,他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洛阳牡丹甲天下,文奇来自中石化。”读到此,我笑了,感到很亲切也很欣慰。我到鲁院看望文奇时,正值他们高研班和《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一起组成“同行诗社”,开展“母亲节手电筒诗会”活动,他们真诚邀请我参加。从他老师和同学的口中,我听到了大家对洛阳文坛的熟悉、对洛阳市作协良好的评价,想必这些都是文奇做的宣传。同时,我感觉文奇爱家乡、重感情。他在书中写到:“离家两个多月了,在千里之外得到老家人的盛情款待,听着纯正乡音,诉说家乡事情,我一度恍惚真有点在家的感觉,酒不免就多了点。饭后,他们两口子又坚持把我送到地铁口。下地铁站时,嫂夫人用洛阳话和我道别,一刹那,眼泪又莫名涌了出来。含着眼泪,向他们鞠躬道别。”无情未必真豪杰,读到此处,我颇有感触。“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个人,要有归属感,如果没有了故乡、没有了朋友,那么,他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家园将会严重缺失。“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砥砺前行!
其次,文奇的创作毅力让我钦佩。文学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和荆棘。文学创作纯属个体劳动,是一个很自我的工作,没有谁逼你去创作,写作者需要自我加压,与自身的困苦、懒惰、犹豫、彷徨等因素做斗争,这个过程,与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相类似。要想赢得读者,必须先要战胜自己。而创作毅力,是作家战胜自我最有力的武器。在短短四个月间,除去正常学习和创作时间,文奇撰写了这本近25万字的书,实属不易。他在书中讲到:“整理学习笔记非常艰苦,过程枯燥繁琐。老师一堂课发言的字数大多在15000至20000字之间,我先要把这些内容在电脑上打出来,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删减。而我仅会拼音打字,每分钟只能打出30来个字,笔记整理得比较慢。除上课外,我尽量减少外出,独自在宿舍整理笔记。晚上每每整理告一段落时,大都已至凌晨一两点钟;还有几次,抬头一看,窗外已是大亮。这样的情况,从来鲁院以后基本如此。两个月了,或许过了热情期,自己感到身心俱疲,加上常常上火,口舌生疮,嗓子红肿,吃饭难以下咽,每每躺在床上,就如掉进了万丈深渊。”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讲,点灯熬夜、通宵伏案的滋味大都经历过,但一直坚持数月天天如此,人数恐怕就有限了。“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文奇对文学的这种勤奋和坚韧,实在让我佩服,但同时我也希望文奇更要保重身体。
第三,文奇是个十分富于情感和念情感恩之人。书中自始至终倾注了文奇的款款深情,前前后后皆流露出感恩之意。他谈到了对自己父母和家人的感恩,对培养他的洛阳石化、中国石化的感恩,对鲁院、老师和同学的感恩,对到鲁院看望他的领导、朋友们的感恩,对天地人间、世界万物的感恩。书中他写到:“自己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岁月不仅染白了头发,而且也赠予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时光更替中,自己的天性似乎并没有被改变——富于感情、容易怀旧、感恩念情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日益加深了。我很多次地站在宿舍的窗前,面对西方的天空,久久地看着夕阳余晖中,万物都沐浴着阳光的脉脉温情,心生无限感慨。很多天来,尽管是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渡过了漫漫长夜,但我内心深处从没有感觉到过孤单和寂寥,不管我是困乏还是劳累,不管我是忧愁还是欢乐,我的心底里始终有光明存在,有希望向我招手。我常常觉得亲人、朋友、领导都在陪伴着我。我常与他们进行对话,常看到他们对我发出期待而温润的眼神,我在心中向他们保证了无数次,一定要用好的作品来回报大家的关爱!我打开窗户,夜幕中的北京小雨淅淅沥沥、飞飞扬扬,打湿了远处飘来的灯光,送来了稍有腥味的泥土气息。我伸出手去,在这湿润的世界里迎接着上苍对我的恩赐,接纳着黑暗中那属于我的片片光明。”万事德为先,做文,先做人。意思就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而感恩念情、知恩图报正是做人重要的品质之一。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文奇是个乐意奉献、敢于作为、勇于担当之人。在市作协日常工作中,文奇强烈的责任心和不打折扣的执行力,大家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在这本书中,也体现出了他的“一诺千金”。在后记中他讲到:“在即将奔赴鲁院的前夕,文友为我饯行。大家对我讲:你到鲁院后,要做好学习笔记,等你归来,我们要阅读你的笔记。要知道,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向往鲁院,鲁院也是我们大家的梦想。对此要求,我当即应下了。因为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们,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基层文学爱好者对学习的渴望。”答应下来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语,但要把这句话语落实下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自己仅会拼音打字,进度很慢,长时间坐在电脑前,腰椎、颈椎和肩膀又困又木;还有眼睛,盯屏幕时间过长,苦涩酸痛,严重时只能眯着个眼缝看屏幕。”尽管如此,文奇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不仅带给了文友们一份合格的学习记录,而且也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打开了鲁院的一扇窗。我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先生曾经讲:“真正进步的决不以‘孤独’‘进步’为己足,必须负起责任,使大家都进步,至少使周围的人都进步。”从这个角度看,文奇的这部书确实反映出了他心中有一份大爱和责任。
掩卷深思,心仍激荡。除品悟文奇之心性、之情怀外,我也陷入了对当下时代、当下文学的感慨。
今年11月30日,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谈到文艺创作时,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他同时希望作家要“胸中有大义,心中有人民。肩上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写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时代在前进,文学也在不断完善。每一个时期,文学的“当下”和语境都在变化。当代,在创作思想上,我们如何用文学的经验和叙述穿透生命、穿透心灵、刺穿灵魂?如何用文学完成自我审判、自我救赎?如何树立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找到苦难的根源,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如何在历史的纵深之外,再有国际视野的宽度,从世界的思潮异动和历史的选择这个坐标考量把握当下的中国,刮去水面上越积越厚的油花,显示出被遮蔽了的人性真相?如何寻找、发现和看到当今中国人心灵的幽微之处,辨认出我们自己的模样,触碰唤醒灵魂阴影中的那片存在与经验的碎片森林,进而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在创作技术上,如何处理好经验的叙述和情景的描述?文学叙写中“虚”“实”如何转换?如何将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如何实现语言和语境的文学“在场”?如何把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当代“城市文学”的发展进程?如何适应目前反抒情、多思辩、突破常规的写作实践?现代审美范式的转变、突破二元对立的精神体验,在构架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时,在赋予新内涵的书写场域中如何呈现?等等,等等。
这些基层作者困惑的、急需了解的、能够提升眼界、拓宽视野的文学问题,尽管这本书中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通过阅读这本书或许会使大家灵光一现,得到一些启发和启迪。至少,我读了文奇这本书稿之后就产生了以上的联想。
文学是神圣的,也是纯粹的。文学中无论是长河落日、大漠云烟,还是春风化雨、春光迤逦,最终都要指向心灵的叩问,灵魂的升华。
《诗经》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相借鉴、触类旁通,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能力和基础手段。希望文奇这本书,能对更多的文学作者、文学爱好者,在提升自我创作水平和写作技巧上带来启迪和帮助。我想,这应该也是文奇先生创作这本书的初衷!
2016年12月8日
(作者系河南省作协理事、洛阳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