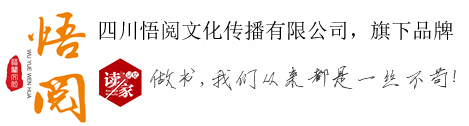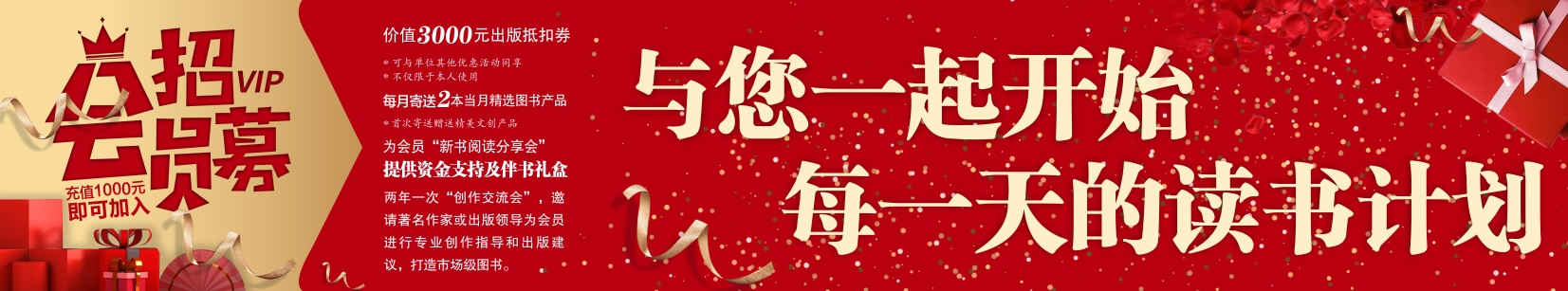028-86613050
18581836866
精彩书评
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 精彩书评
《50度》序言
我知道的康泾
柯 平
一个幸运的写作者,在读大学时候搭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高潮的末班车,在经受过朦胧诗和第三代的双重洗礼以后,返回了他的家乡,先是做教师,后进入机关长期从事行政工作。从艾略特庞德北岛海子到文件讲稿宣传材料考察报告,这个过程的艰难复杂可想而知,不知道这些年来他是怎样在内心协调并坚持过来的,只知道手中写诗的笔一直没放下来过。这让我想起金庸小说里的一个著名人物周伯通,两手能分别使出不同的武功来。我这人做事一根筋,心里有他事搁着,就写不好东西,为此一生中基本没正儿八经上过班。对他的这种本事,因此也就特别的佩服。
再以后,他可能因职务变动的缘故,加上又兼任了地方文学界的领导,对诗歌的热情再度被疯狂燃起,而这时诗坛已早非昔比,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各种新技术的流行,开山立门,竞奇斗巧俨然已为主流,诗歌的重心也逐渐向技艺和形式转移,这或许会让他稍有几分迷惘。好在他又是明智的,深知自己跟绝大多数写诗的人一样,并不为诗神所特别恩宠,赐以格外的天分,也就因为年轻时爱上了丢不下,不写心里就难受罢了。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修辞固然让人神往,但如果不具备这个本事,刻意求之,弄得不好反有以辞害意的危险。与其趋时附势,不如扬长避短。拿出自己最擅长的功夫来,即注重理性思辨的力量。实际上这从诗的标题和叙述语调也可看得出来,典型的玄学派风格,师法自然,取材随意,结构精巧,叙述老到,且每多言外之意,题外之旨。想象中,他应该喜欢宋诗,或西方的前辈大师如约翰多恩之类,只是没问过他,不敢保证。但曾记多恩昔有名言曰:“少狎诗歌,老娶神学。”如移用在他的身上,倒是多少也有些切合的。
康泾写诗,大致就是这么写的,他善于以略带荒诞的语言方式来解剖身边的现实,以冷嘲热讽为主打武器,将主观感情色彩减至最低,或隔山打牛,或指鹿为马,或声东击西,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跟自己说话,或与假想中的听众进行交谈的过程。凸现在诗集里的诗人形象,时而严肃而深沉,时而嬉皮而放诞。他对自己的要求或许有很多,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赋予日常事物中以思维的光泽,无论是《象棋》、《园丁》,还是《短短几天,一块石头变成了花朵》等,无不笼吟咏对象于形而上之色彩中,这使他的作品与我熟悉的本省其他作者多少有些不同。即便他写《地震》,也会旁敲侧击,只说:“人类的恭敬席卷一空/一切美好浓缩在狭窄的器官里/丑陋,甚至让人来不及爱上一次”。写《一枚钉子》,也会蹊径旁通,诡称:“侵占木头身体的一部分/将牺牲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截”。
这让我不免想起特朗斯特罗姆笔下的舒伯特的形象:“他戴着眼镜睡觉,每天早晨准时站在高高的写字台前。/当他写乐谱时奇妙的蜈蚣便开始在纸上爬动。”(黄灿然译)在某种意义上,康泾的诗,也有点像是这样一些奇妙的蜈蚣,貌似无关紧要的谈天说地,自言自语中,实际上有许多尖锐的触须隐藏在言词的身体下面,冷不防就会蜇你一下。尽管整体上尚欠完美,有晦涩或过于随意之嫌,但反过来说,自然与随便,浑厚与混浊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或许更能展示其真实状态。而康泾的价值,就在于他写出来的是康泾,而不是康桥或者康山。有道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歌实际上在我们心目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神秘的伊人的角色,而写诗就是为了弄清她的真面目,包括她那美妙的身体结构。因此,有向上半身求之者,有向下半身求之者,有向四肢求之者,有向脖子以上部分即嘴脸求之者,亦有向身体以外求之者,大家目的相同,没什么高下之分,而康泾爱向螓首脑际甚至脑壳内部求之,自然也没什么不可以。
此外,他对诗的感情和文人气质也体现在其他的种种方面,如担任地方作家协会的主席,组织诗会,举办讲座,主编诗集,培养新人,做了大量有益于文学的事情。同时,他还是一名有成效的地方大儒吕留良的研究者。这些情况,我都是从网络或别人口里了解到的。虽说相识甚早,相见更亲,只是我中年以后生性疏懒,倦于交游,两地相隔仅只百里,平时却来往无多。但碰到嘉兴的朋友时总会记得问一下,或有时看到有关桐乡的新闻,就会好奇地想,不知康泾此刻在干什么?不会又陪省里或北京来的领导下基层考察,或组织写作班子起草市委的讲话材料了吧,心中多少会有一些忧虑。这次蒙他以新作见示,并以序事相属,气息纯正、文字干净,严谨的思考中略带一丝迷惘和无奈,完全不像是一个整天跟政策文件打交道的人写出来的,这才终于放下心来。
(作者系浙江省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著名诗人)